山中无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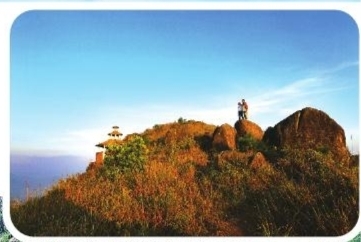
锣鼓山落日 刘岩生 摄

凤阳村俯瞰 缪福森 摄
每次回故乡,都会到山里转转,看看芒萁温柔的身影,闻闻松针淡淡的香味,一成不变的景致,仿佛时光凝滞。在山里走着走着,就回到了童年,心里装满简单的快乐。倏而之间,山外世界的牵挂、压力、沮丧、无助、绝望,都了无踪影。
向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它让我们富有激情、努力拼搏、永不止步;向后是心灵宁静的港湾,它使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宽容自己,进而心平气和地与自己友好相处。大多时候,我们都是庸常的人,比起前行的激情,更需要从记忆深处寻找心灵的慰藉。
童年烙上山的印迹,一生就绕不过对山的热爱。从神山冈仁波齐到仙山蓬莱,从东岳泰山到西岳华山,一生不曾停止过寻山的脚步。不仅如此,我学在长安山,住在乌山,讨生活在屏山,山山不断,生不离山。其实,我绕不过的还是童年,因为每次新到一座山,我就仿佛回到童年,赶着我放牧的那只母羊走进故乡的深山。
二
到凤阳,白天登锣鼓山,夜晚住白云山。
锣鼓山与白云山遥遥相对,中间有黄兰溪湖,有大小村落,有葡萄园,人在其中,渺小如尘,但却也因为在山中,灵魂舒坦无比。
午后上锣鼓山,一群人结伴,徐徐而行。山岭悠长,直抵山顶。沿路两旁有香菇子、地稔、乌饭树,一如四十年前故乡山间给我的记忆。摘一把熟透的地稔放入口中,酸甜中略带涩味。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只是味蕾已经不是当初的味蕾了。
六岁那年,学前,我在离锣鼓山几十公里之外的南山脚下放羊。故事开始于父亲某一天的心血来潮,他到镇上买了一只母羊,让我赶着,与邻居大哥大姐一起进山。六岁的我,根本跑不过母羊,不过不碍事,一遇到羊群,母羊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快乐。我们把羊群赶上山坡,人远远地坐在一块名叫“纱帽岩”的石头上,看着羊群越走越远,慢慢融入了天际边的白云之中。
放羊的这一年,我认识了山里的野果,可以药用的青草,也受过毒蛇的惊吓,野蜂的攻击。没有多久,学会了光脚在山野的小路上奔跑,把欺负母羊的公羊撵得四处逃窜。可我还是没有保护好母羊,它怀孕了,在我结束放羊生涯的秋天生下了一只小羊。
如果没有童年的这段经历,我应该体会不到锣鼓山向我们展示的莫大善意,我闻到的,尝到的,脚底感觉到的,都是童年记忆在脑海中的反刍。
锣鼓山与白云山有两个不同版本的传说,不管是姊妹反目成仇,还是一同受到玉帝责罚,都是为了说明两座大山的不同形态。白云山巍峨挺拔,山间却沟壑纵横,仿佛遍体鳞伤;锣鼓山头平腰鼓,好像受过重力扣压。白云山的伤痕是冰臼,白云山因此被列为世界地质公园遗址。相比之下,敦厚浑圆的锣鼓山显得籍籍无名。但是,这并不妨碍凤阳人对锣鼓山的膜拜,人们在山间修建寺庙,在山顶立碑勒石,满心虔诚地传唱它的伟岸。
锣鼓山是否钟灵毓秀,可以看看它山脚的子民。有我在二中教书时的同仁,物理强人郑仕标,一个人有200多篇论文被SCI收录,可以顶上一所大学;有我的文友,文字锦绣的徐锦斌、刘岩生……
我不确定这些才俊的成名与锣鼓山之间到底有多大关系,但我确定,每一座大山,都有它自己的故事。不管山外的世界如何巨变,也不管来看它的人是科学家、诗人、作家,还是一个放羊的孩子,它都一样,开该开的花,结该结的果。
三
山里的地名,一种直截了当,比如锣鼓山,表示一座像锣鼓一样的山;另一种是与事实相反,只是表达美好的愿望,锣鼓山下的凤阳村就是。
凤阳以前叫棠洋。叫洋的地方,多有水,而且平坦开阔,事实上,这只是一个隐藏在丘陵之间的村落,与“洋”真的没有多大关系,但作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又何妨?凤阳人并不满足于“洋”的平坦,他们还希望能“五凤翔集”“丹凤朝阳”,所以后来又改名叫风池、凤翔,最后于民国年间,叫成了今天的名字——凤阳。
不管是一个地方,还是一个人,名字的意义都很深远,它会给人暗示,在潜意识里影响认知和行动。
中国叫凤阳的地方不在少数,安徽凤阳还出了朱皇帝。寿宁山里的凤阳也出皇帝,他们的皇帝出在北路戏里。
寿宁北路戏俗称福建乱弹、横哨戏,源于清代中叶传入福建的乱弹与当地民间戏曲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地方剧种,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北路戏为什么会在凤阳乡的廷加洋村发祥,一切不得而知。
传入福建的乱弹先后产生了上路班、下路班、北路班、南路班等戏班,二三百年间,除了活跃在山里的北路班外,其他各路相继解散。北路班的存继也并非一帆风顺,有过“阿楷班”带领诸多戏班,穿梭演出于闽浙乡间的繁荣景象,也有过“戏台冷落声渐悄,剧本荒芜演员无”的濒危时刻。好在,2006年寿宁县成功申报寿宁北路戏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此,锣鼓山下,北路戏横哨再度响起,锣鼓“咚咚锵”的声音铿锵有力。
戏如人生,起起落落,兴衰成败,都是常态。只是在凤阳村的刘氏祠堂看过《廊桥神医》演出之后,不得不感叹,是这片山水滋养了这个珍稀剧种。
寿宁人爱戏,深入骨髓之中。
放羊生涯中,我唯一与人打过的一架就是因戏而起。小伙伴们躺在“纱帽岩”上讨论传说中的村里戏班,话题的焦点是自己的父亲当初演什么角色,有的是皇帝,有的是奸臣,有的是梅香,各种角色都被说光了,我只好说我爸演的是奴才。没有料到有人起哄,说我爸从小读书,什么也没演过。连奴才都不让演,简直是奇耻大辱,我只能挥拳相向。
凤阳人爱戏有过之而无不及。逢重大节庆活动和来客观摩,几个葡萄园里回来的泥腿子连夜合计,三五天时间准能凑一出传统折子铿锵出场。甚至,某场临时排演的戏里,哪位老牌演员缺席戏份了,难免还会私下里吃起“戏醋”来……
人生如戏,人生怎么可以无戏呢?
朝入农田的乡民,夜里登上戏台,可以穿越唐宋,神游明清;可以黄袍马褂,念一句“文官把笔安天下,武将提刀定太平”,或者充满憧憬地唱道“今日苦读守寒门,明朝骑马进高楼……”方寸舞台之间,王侯将相,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应有尽有。
戏终归是戏,一折《穆桂英挂帅》五十年前演出的内容,与昨天我在刘氏祠堂看到的情景,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山里的岁月,如戏一般,周而复始,凝滞不动。
我最喜欢的还是《齐王哭将》里钟离春班师凯旋的场景,不说那种捧迎的皇家气派,就冲那场久别重逢的惊喜,也让我心有戚戚。
人类追求快乐的过程,其实就是前进、回首,再前进、再回首的不断轮回交替。于是,我们需要日异月殊的城市,也需要岁月凝滞的山村。
附件下载
-
中央部委网站
- 外交部
- 国防部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教育部
- 科学技术部
- 工业和信息化部
-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 公安部
- 国家安全部
- 民政部
- 司法部
- 财政部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 自然资源部
- 生态环境部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交通运输部
- 水利部
- 农业农村部
- 商务部
- 文化和旅游部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退役军人事务部
- 应急管理部
- 中国人民银行
- 审计署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 国家航天局
- 国家原子能机构
- 国家外国专家局
- 国家海洋局
- 国家核安全局
- 国家乡村振兴局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海关总署
- 国家税务总局
-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 国家体育总局
- 国家信访局
- 国家统计局
- 国家知识产权局
-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 国家医疗保障局
- 国务院参事室
-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 国家反垄断局
-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 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
- 国家宗教事务局
- 国务院研究室
-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新华通讯社
- 中国科学院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中国工程院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 中国气象局
- 国家行政学院
-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 国家能源局
- 国家数据局
-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 国家烟草专卖局
- 国家移民管理局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 国家铁路局
- 中国民用航空局
- 国家邮政局
- 国家文物局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 国家消防救援局
- 国家外汇管理局
-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
省、市政府网站
-
设区市政府网站
-
市政府部门网站
-
县(市、区)政府网站
-
其他
-
中央部委网站
- 外交部
- 国防部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教育部
- 科学技术部
- 工业和信息化部
-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 公安部
- 国家安全部
- 民政部
- 司法部
- 财政部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 自然资源部
- 生态环境部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交通运输部
- 水利部
- 农业农村部
- 商务部
- 文化和旅游部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退役军人事务部
- 应急管理部
- 中国人民银行
- 审计署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 国家航天局
- 国家原子能机构
- 国家外国专家局
- 国家海洋局
- 国家核安全局
- 国家乡村振兴局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海关总署
- 国家税务总局
-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 国家体育总局
- 国家信访局
- 国家统计局
- 国家知识产权局
-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 国家医疗保障局
- 国务院参事室
-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 国家反垄断局
-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 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
- 国家宗教事务局
- 国务院研究室
-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新华通讯社
- 中国科学院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中国工程院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 中国气象局
- 国家行政学院
-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 国家能源局
- 国家数据局
-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 国家烟草专卖局
- 国家移民管理局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 国家铁路局
- 中国民用航空局
- 国家邮政局
- 国家文物局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 国家消防救援局
- 国家外汇管理局
-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
省、市政府网站
-
设区市政府网站
-
市政府部门网站
-
县(市、区)政府网站
-
其他
联系我们| 站点地图| 隐私保护| 关于我们| 法律声明| 收藏本站 收藏本站 取消收藏本站
网站标识码:3509000001
 闽公网安备:35099902000024号
闽ICP备11005255号
闽公网安备:35099902000024号
闽ICP备11005255号
版权所有:宁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主办: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为确保最佳浏览效果,建议您使用以下浏览器版本:IE浏览器9.0版本及以上; Google Chrome浏览器 63版本及以上; 360浏览器9.1版本及以上,且IE内核9.0及以上。




